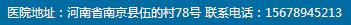当前位置:带状疱疹性脑膜炎 > 饮食调养 > 十苦九难出头尽不苦不难不成人浦江盲艺 >
十苦九难出头尽不苦不难不成人浦江盲艺
几天前,当我得知已经九十三岁高龄的洪兰书依然健在的消息后,唤醒沉睡已久的记忆,特地从杭州赶回浦江县黄宅镇新店村,一探究竟。
拜了两个师傅年,洪兰书出生在浦江县黄宅镇后江村的一户贫困人家。家里除了父母,只有兄妹两个,上面还有一个哥哥。
周岁的时候,洪兰书脸上生疮。因为家里穷,没有饭吃,更没有钱治疗,病情越来越重,整张脸都烂了,烂到眼睛,致使双目失明。
盲人要才能养活自己,需要一技之长。七岁那年,妈妈安排洪兰书到下于桥头村,拜唱新闻的盲艺人于小大为师。妈妈在纱巾里包了三斤米,叫她在师傅家搭伙。师傅家没有床,她就睡在地上。
几天时间,师傅教她学唱一段劝世文:
好人不拌口,君子不报仇。
君子报仇该三年,小人出气在眼前。
君子不该去听小人,小人的大话不该听。
好话听了多礼经,当面跟我们同家人。
老好人是活死人,走转背后就弄送。
这面挑么那面哄,小事弄作平天公。
口食别家的无头酒,要用别家的无头银。
暗算别人一千,自划到八百份。
运道不到还没到,运道到了总回报。
洪兰书当时年纪小,还不懂事,听别人说唱新闻就是讨饭吃,没过几天,就跑回家,不去学了。
到了十岁那年,妈妈把洪兰书送到桐木殿朱宅村,拜盲艺人朱真文为师,学唱正本,前后点名三年。
因为家里穷,缴不起学费,妈妈就挑几秤粟米给师傅,算是朋友帮忙。住在师傅家里,吃饭的米是家里带去的,菜干也带一点去,有时向隔壁邻舍讨一点。
一张嘴巴和两种乐器的奇妙世界唱新闻是一种将戏曲、相声、歌谣、说书和口技等众多民间艺术熔于一炉的综合艺术,靠一张嘴巴和两种乐器:渔鼓和竹夹。盲艺人用手指敲击渔鼓的鼓边,发出“笃”的声音,手掌敲击渔鼓的鼓心,发出“仓”的声音,夹板夹击,发出“吉”的声音。同时,敲击渔鼓可用一个手指,或者多个手指,或者整个手掌,发出的声音或轻或重,或急或缓。新闻的唱词可长可短,以七字句为主,也有三字句、五字句、九字句,甚至十多字句,可以句句押韵,也可以隔句押韵。这样,一张嘴巴,两种乐器,发出多种声音,就像一堂喧闹的鼓。
跟唱戏有剧头、正本和连台本戏一样,唱新闻有滩头、正本和长篇。要唱新闻滩头戏,洪兰书先唱一段滩头,相当于戏曲里的剧头,既可酝酿气氛,也可吸引更多的听众;再唱正本,大约两到四个小时;还有更长的长篇,可唱三天,相当于戏曲的连台本。家乡浦江道情的传统剧目,有一百二十多本正本,五十多个滩头,一般演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三教九流的故事,不外乎忠孝节义、除暴安良、劫富济贫等内容。
洪兰书说,唱新闻有一定的套路。正本的开篇,可以这样唱:“自从盘古分天地,先有新闻后有戏。”“出新闻来道新闻,新闻要唱哪州哪府哪家门。”“中国两京十八省,新闻要唱哪一省?新闻要唱浙江省。浙江省要唱哪一府?浙江省唱到金华府。金华府金华县,金华里头唱哪家门?金华要唱梅花门,离城官路三十里,岭下朱村坊编新闻,姓朱就是朱家门。”正本的承接,可以这样唱:“停停歇歇再提起,前有新闻都唱齐(尽),后有新闻再提起(随后跟),(接下去)新闻唱本《弓弹记》。《弓弹记》为本戏,路头路角唱不齐(尽),赶船赶路不提门。掇记马头翻记身,要唱新闻哪个人?调一头翻一身,唱一家扔一户,为什么事情编新闻?为什么事情起祸根?”正本的结尾,可以这样唱:“十苦九难出头尽,不苦不难不成人。十苦九难大翻身,发子发孙几年春。团团圆圆有一户,到这里过出头尽。”
洪兰书眼睛看不见,可记忆力惊人,这辈子跟师傅学了好几十本戏:会唱的滩头有《管老婆》《偷鸡记》《卖桃记》《黑麻痢》《廿三个老公》《宝瓶记》等;正本有《分玉镯》《情义缘》《绣书袱》《描金凤》《龙凤带》《玉连环》《雌雄福》《玉龙宝珠》《玉如意》《拐子记》《红蛇记》《二环记》《七星剑》《百花龙袍》《玉环记》《玉金鸡》等;几十年来,还与夜渔市村的黄湖亭一起,每年两次到县文化馆、广播站,演唱宣传国家新政策的资料,包括三反五反、破旧立新、四清运动、计划生育、农业纲要十四条、农业学大寨、粉碎四人帮、新婚姻法等。
洪兰书还有一样特殊的本领,就是善于穿针。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确是千真万确。亮眼的邻居穿不了,就叫她帮忙穿。她穿针并不是用眼睛看,而是凭盲人敏锐的感觉,指头与针线之间的感觉。
出门演唱的三个阶段为了谋生,洪兰书这辈子走街串户,跑遍家乡的每个乡镇。
她的演唱,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我推销。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名气还没有唱出来,找到歇家后,唱两句听听看。歇家听了觉得好,就留她唱一夜。去七邻八舍凑粮食,你一碗,我半碗,大约是十廿斤。谷收季节要米,麦收季节要麦,最后卖给村民,换成钞票,便于携带。也可凑钱,随行就市,金额并不一定。唱一夜新闻,户家要请她吃三顿饭:当天的晚饭、夜茶和第二天的早餐。假如是上午定下来的,还要加一餐午饭。如果无人请,就要饿肚皮,只得“压”给农家。先向农家借宿,再软磨烂缠,价钱便宜一点,十有八九能成,因为当时乡村的文娱生活极度贫乏,新闻通俗易懂,明白如话,受到男女老少的青睐。如果实在无人请,就是没有报酬也要唱,吃和住总有着落。像花桥台头塆村的季四球热情好客,加上娘家在县城的东门外岳塘桥头,对于东门外来的盲艺人特别客气。洪兰书第一次去花桥台头塆村唱新闻,就住在季四球家。第二阶段,歇家介绍。她的演唱艺术得到认可后,下次再去,歇家会主动帮她介绍,兜揽生意,省心多了。第三阶段,主动邀请。得到听众普遍认可,有了名气以后,坐在家里,也会有人上门邀请。有时候,在一个村坊唱新闻,唱得动听,邻近村坊的听众受到感动,争相邀请她去演唱。这时候,因为分身乏术,甚至会出现听众抢夺渔鼓的现象。
如果遇到人家办喜宴,她去宴席上唱祝愿新郎新娘早生贵子之类的利市戏。新郎家请她体体面面吃一顿,并赠送红蛋和果子之类的礼物,参加婚宴的宾客出一点钱,多少随喜。
洪兰书说,唱新闻也要讲规矩,敬大爱小。一般而言,师傅唱熟的地盘,徒弟不能去唱,除非是特意邀请。有一次,她在婚宴上无意中碰见师爷爷朱志宁,就让给他唱。到了最后,她才唱了两句利市戏,拿一次钱。
有眼天上,无眼地狱有道是“当官的爷,不如讨饭的娘”。作为一个母亲,都会精心关心照料自己的孩子,而盲人因为生理缺陷,双目失明,在这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洪兰书这辈子生了六个孩子,四男两女,因为生活困难,一个儿子从小送给人家。子女出生以后,她无法很好地照料他们,只能叫丈夫带大。幼子出生不久,为了早日出门唱新闻赚钱,早早给他断奶。到了晚上,幼子肚饥,啼哭不止,就把糖蔗塞进幼子的嘴里,哄他入睡。
洪兰书的丈夫腿部残疾,不良于行,却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犁耕耙耖,样样在行。在大集体时代,当了多年的生产队长。即便如此,因为子女多,负担重,每年都是缺粮户。作为一个残疾人,他既当爹,又当娘,日子过得格外艰辛。
光靠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丈夫一个人,养活不了全家,洪兰书孤身出门,常年四处奔波,靠唱新闻赚取微薄收入,补贴家用。
俗话说“有眼天上,无眼地狱”,一年到头,翻山越岭,风吹雨淋,洪兰书靠一双脚和一根探路的竹棒,跑遍浦江的各个乡村,吃尽人间的苦头。每次到山里,一去就是一月。留在家里的孩子长时间见不到娘,格外可怜;而她想起孩子孤苦伶仃,多了一份牵肠挂肚。三子在三到七岁之间,跟着她在西部山区跋山涉水。七岁那年,在杭口坪的深山里,三子高烧不退,急得她六神无主,赶紧雇人送回家里,医院,原来得了脑膜炎。
有时家里断粮,孩子们嗷嗷待哺。洪兰书就向隔壁邻舍借粮,半斤一斤,借遍全村的七十二户人家,全部记在脑子里。三子在中山中学读高中的时候,每周从家里带去四斤米,经常是向邻居借的。等到自家有了粮食,再一家一家归还,不会有半点差错。
没得吃,也没得穿。到了很冷的冬天,孩子们只穿一根单裤,冻得瑟瑟发抖,还可能是向别人讨来的。洪兰书自己也经常衣不蔽体,有一次出门,发现屁股部位有个大洞,就用笠帽遮住。
过个八月十三花掉两月收入日子虽然过得很艰辛,洪兰书很坚强,也很乐观,并不觉得有多少苦。她说,自己人缘好,每到一地,有人哀怜,那些打小铁的师傅才真叫可怜,晚上无处居住,就睡在凉亭破庙、堂楼走廊上。她的人缘,除了新闻唱得好,人长得清清楚楚,衣服穿得干干净净,说话规规矩矩,做人老老实实。
洪兰书出门在外,得人帮助,受人恩惠,并没有忘记他们,尤其是山里的歇家。每年农历八月十三,是祭祀胡公的庙会,也是黄宅的物资交流大会。山里的歇家有的背一根竹,有的背一根树,走了几十里路,来黄宅参加物资交流大会,人生地疏,举目无亲,都来她家吃饭。
每年到了八月初,洪兰书家就忙开了,准备八月十三招待客人的酒菜,比过年还要体面。家里预先准备两灶豆腐,两酒坛兰花豆,两酒坛泥鳅干,一槽篓豆芽菜,一脚桶海带,一脸盆红烧肉,还有茭白、藕等食品。一个时节过下来,招待客人吃饭的费用,相当于她唱新闻两个月的收入。
正如新闻里唱的那样,“十苦九难出头尽,不苦不难不成人”。俱往矣!如今九十三岁的洪兰书苦尽甘来,子女有出息,也孝顺,享受天伦之乐。虽然年迈,行走不便,看起来皮肤滋润,耳朵很亮,口齿清楚,记忆力尚可,身体状况好的时候,还能唱一个滩头戏呢!
作者|王向阳
编辑|陈栋辉
审核|李少俊
广告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