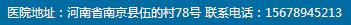当前位置:带状疱疹性脑膜炎 > 预防护理 > 芒市知青岁月第36期张晓明忆松林 >
芒市知青岁月第36期张晓明忆松林
芒市——神奇黎明之城,生态宜居圣地。如花的史实盛开在古老而淳朴的土壤里,请随“史话芒市”一起探索发现那充满希望的火炬冉冉亮起......
?芒市有多美,只有生于斯、长于斯和居于斯、业于斯的人深有体会;芒市有多好,曾经在这里挥洒青春热血的芒市知青最想倾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20世纪50年代,为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他们带着一腔热血和激情,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芒市插队落户和屯垦戍边,与芒市人民同甘共苦、建设“第二故乡”,为芒市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奠定了坚实基础、结下了深厚友谊,是芒市人民最为宝贵的重要精神财富之一。芒市人民将永远铭记他(她)们、感激他(她)们、祝愿他(她)们。为纪念他(她)们这段珍贵的历史,表达芒市人民的感恩之情,更好地激发全市各族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和永远跟党走的坚强意志,芒市委党史研究室特推出“芒市知青岁月”栏目。本周推出第36期,张晓明:忆松林║法帕镇知青║(潞西县知识青年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合影)忆松林
张晓明
岁月流淌,洗刷掉无数的过去,沉淀下来的便是历史,成为人们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我心底,40多年来,一直有一个朴实纯真、温和而又刚毅的知青身影,时常浮现在眼前,他就是我的同窗好友王松林。年的晚秋,他因患急性脑膜炎,连续10多天高烧,但仍天天坚持下地劳动,最终昏倒在田间,再也没有醒过来。19岁,正值青春年华的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充满对未来向往的世界,长眠于芒市法帕镇芒棒寨的竹林中。(傣汉一家人)记得刚进初中时,我们都是住校生,他就睡在我的下床。当时同学们都争着睡上床,而他却没有争,一个人安静地铺上自己单薄的被褥。后来我才知道,他家境贫寒,父亲是一位盲人,在自来水公司开设在街巷里的水龙头处守着收费,一分钱一桶,没日没夜;母亲在一食堂打杂工,起早贪黑。他有一个哥哥,没读几年书,早早就当了学徒工,为的是贴补家用供弟弟读书。全家人把改变家庭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了王松林的身上,可才读到初中二年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那时候住校生的伙食都是按定量供给,男生每月交7.5元,天天嚷肚子饿。记得有一次,别班的男生和我们打赌,看谁能一口气吃下两把面条(每把一斤)。大家正犹豫时,松林站出来说:“我能。”我们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因为平时很少听到他说没吃饱。后来,那同学真的拿来两把干面条,又宽又黑,我们一起拿到食堂煮了。松林就当着大家有滋有味地把这酱油素面一口气吃得干干净净,吃完后抹一抹嘴,什么也没说,大家也都无话可说。这一幕留在我心里好多年。不难想象,平日里,他默默地忍受了多少饥饿与困苦。松林的身材和我差不多,在班上男生里属中等身高。上体育课时,老师按高矮次序,把大一点的同学排在大大队,小一点的排在小小队。我们俩正好排在小小队的头里,他每次排队前都要和我比一下高矮。他总以为自己长得更快,但往往又不得不让我站第一。其实有几次我微微踮起脚尖,他力争第一的劲头被我很多次打压。他去世后,我想起这事,鼻子就发酸。他和我们一样很喜欢打篮球。下课后,男生们都冲向球场,他却经常来得晚,因为有几个爱玩的男生一到卫生值日的时候就让他顶替,他也二话不说。等他打扫完卫生来到球场,我们已经开打了。他只好在球场边看着,有时自己围着球场跑几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都去大串联,我们班一些男生相约长征走到北京。学校担心会出事,不允许,我们大家就一起坐火车到了贵阳。王松林和我们班另外4个男生又来约我徒步长征,我没有勇气。他们一行5个人就由贵阳出发,从年11月份一直走到年2月底才到达北京。那时大串联已经结束,他们在北京住了几天就被送了回来。在学校里突然看到他们时,大家都很惊喜。我看到他身上的衣服有很多补丁,裤子的内侧全磨损了,听一起去的同学说,这些补丁都是他一路上自己缝补的。而他脸上展示的是胜利的自信和坚强。其他人是怎么走过来的,我没有多想,因为在贵阳分手的时候,我看到他身上的衣服最单薄,行装最简单。几个15岁的男孩,在整个冬天里从南方一步一步走向寒冷的北方,这要多大的毅力啊!好多年后一想起来,我都由衷地敬佩。尽管松林没有见到毛主席,但我觉得他比我们见到毛主席的还值。知识青年下乡前,在外游荡的同学们都回到了学校。大家一见松林,都眼前一亮,一年多没见,他竟长得又高又壮,笑眯眯的脸上透出男子汉的刚毅和自信。一个曾在大大队的男生试图挑战他,他就用单臂做了几个俯卧撑和引体向上。大家都赞赏不已,心想他一定是利用这一年多的时间为家里做了很多事,劳动锻炼使他变得更健壮、更成熟。下乡后,我们俩没有分在同一个寨子。我和班上几个男生在法帕寨,他在芒棒寨,但两个寨子相邻,田地也是连着的,出工时还能遇到。一开始,知青们不会农活,工分评得都很低,一天只有三四分,知青们都不满。没过多久,我就听说王松林的工分能评到8分;半年后,他就被评为标兵分——10分,令人羡慕不已。可我知道,这是他吃苦耐劳拼命干出来的。知青们经常会到县城赶集,可他却坚持天天出工,从未看到过他闲暇的身影。(40年弹指一挥过,芒市河知青两依旧)我们两个寨子都在坝区,烧柴很困难,常常要去很远的山上挑柴。一次,生产队组织我们去党良(地名)山上砍柴,路上正好遇上他们队也去砍柴,他挑的两个箩筐特别大,大家还笑话他。在山上,我们都把箩筐装得满满的,我们俩的担子特特别重,一个人根本无法挑上肩,只好让其他知青一边一人帮我们抬上肩。他说要一口气挑回寨子,怕半路上放下休息就再也上不了肩,我也答应跟着他一口气挑到寨子。从党良到法帕有10来公里路程,我俩大步走在前面。很快,后面的人就没影了。开始我还行,尽管汗如雨下,还紧跟着他,但后来就得咬紧牙关坚持。而他却一路上快乐地边走边唱,担子在肩上一闪一闪地伴随着他的歌声,很有节奏。终于,看到我们法帕寨了,我也鼓足了劲儿,硬是一口气挑到寨子。他却还有一段路,我放下担子后,看着他迈着坚定脚步渐渐远去的身影,心想,这真成了扎根农村的好农民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挑的担子足有60多公斤,这是我一生中走得最艰难的一段路。年秋收时节,一天夜里下了一场大暴雨,天刚亮就听到上工的钟声,原来是发大水,一大片低洼田里已收割的稻子正在被冲走。我们男知青和小卜冒跟着队长冲到与芒棒田地相连的田边,这里已是汪洋一片,中间一条河水汹涌地将漂浮的水稻冲走,上游的水还在不断涌来。这时,芒棒的人也赶来了,王松林就在其中。队长指着上游的河道说,那边有一条岔河,口上有一道土坝,是为了提高水位灌田打的临时坝,必须把它拆了,让河水分流,才能阻止水稻被冲走。大家看着汪洋中急流汹涌的河水,正在犹豫间,王松林第一个蹚着1米深的水向河道急流冲过去。队长在岸边叫起来,怕他出事,但他头也不回。我见此情景,也和几个知青一起冲下水去,跟他来到急流翻滚的河边。只见王松林一个猛子扑向急流,奋力向对岸游去,我们也先后跳进去拼命向对岸游。虽然才十几米宽的小河,可水流速度很急,不一会儿,我们就被冲下几十米远,但终于还是抓住了岸边淹没在水中的杂草,我们爬上岸向那道小坝冲去。土坝终于被我们拆开,河水分流而下,汪洋中的水位渐渐下落,水中漂浮的大量水稻停止了流动。队长和社员们都很高兴,看到知青们这么勇敢,都打心眼儿里感动。我们也为自己的勇敢举动带来的成功而高兴。现在回想起来,并不觉得这是年轻人的冲动或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无知,而是这一代知青从骨子里透出的精神:乐观、自信、无畏和坚强。松林有时在晚上也到我们寨子来聊天。我们经常谈起自己的命运,想着怎样才能回昆明找份工作,谈论着如何谈恋爱、什么样的女人好。这种时候,他话虽不多。但津津有味地听着。从他的眼神中看得出,他心里一定在盘算着未来。就在这年秋收之后的一天,芒棒知青跑来说,王松林昏倒在田里,医院。医院,看见他在隔离病床上早已不省人事。医院的同学说,一路上怎么叫他都不答应,可奇怪的是,躺在马车上的他竟唱起了“敬爱的毛主席,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以前,他经常会用歌声排解孤独,这歌声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话语。医生感动地对我们说:“患这种脑膜炎除了连续不断的高烧外,头部的疼痛是常人难以承受的。他在病中还一直坚持劳动,令人敬佩。”医院,成了我们的永别。法帕公社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我为他写了悼词,并代表全班同学致悼词。下葬时若按傣族风俗,墓碑要面向西方,可是我们要求松林的墓碑要面向东方——因为,昆明在芒市的东方,那是松林,也是我们知青的家乡。队长同意了。在芒棒竹林间的坟地里,唯独松林的墓碑朝东,永远望着他期盼的家,上面只刻着让人心碎的7个大字——王松林同学之墓。随着招工返城、学校复招,知青们陆续离开了寨子,各自延续着自己精彩的人生旅程: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天伦之乐,打拼挣钱,买房买车……或苦或乐,都享受着生活。可王松林他,却以这充满乐观、自强、刚毅而憧憬未来的青春形象,永远地留存在我们的脑海中,永远,永远……(作者原系潞西县法帕镇腊掌寨昆明知青)友情提示:
讲好芒市知青故事,表达真挚感恩之情。欢迎当年知青下乡所到乡镇及相关媒体平台,转载发布“芒市知青故事”栏目相关文章,用好芒市知青资源,助推芒市更好发展。转载时请注明转自“史话芒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