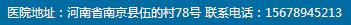安仁站往事
一
安仁,属于衢江区(原衢县),是公社、乡镇所在地。国道和衢江穿边而过,浙赣铁路于年建成时即在此设站,所以附近人通常称“安仁站”,或简称“站里”。七八十年代,安仁因其交通便利,一时成为繁盛之地。
小小的安仁分布着火车客运站、火车货运站、生猪收购站、供销社、综合商店、粮库、生产资料供应站、铁路养路工区、铁路信号工区、犁锅厂、蚕茧站、初中、旅馆、卫生所、邮电所...
图:安仁货运老站台遗址(摄于年)
二
生长在小镇的我,四十年后站在国道边上安仁站小街的入口,在记忆中搜索着故乡的旧模样:国道北边是去郑家、中央徐、欧塘的路,先是一座大沙场,常年堆着沙,也是孩子们天然的娱乐场,沙场北面是一座生猪收购站,生猪被赶上像一段长城城墙似的甬道,甬道尽头是敞开后栏板等着它们的运猪卡车。一条水利渠道就在生猪收购场门口的地下穿过并一直沿公路流向龙游方向。猪场再向里走就是蚕茧站,里面有很原始的水井,打水的方式就像物理书上描述杠杆原理的图。蚕茧站门口,一个上坡就是向欧塘、坎高方向的乡间小道,小道至今尚存。一个下坡就是遍地的桑林,桑林、郑家村和中央徐的后面就是东去的衢江。
三
国道的南面就是安仁站小街,小街的入口处有列车货运站台,铁轨连接着几百米外的浙赣铁路主线,可能是这里有太多的生猪、粮食、河沙需要向外运送。货运站台边上是卫生所有一个大台子,闲时晒谷,也放露天电影,小时候百看不烦的《上甘岭》是在这里放的。模糊地记得有戴高帽的人在这里示众游街过,或许应该是文革晚期。再沿着小街方向走是安仁公社所在地,就是后来的乡镇政府,是个严肃的地方,作为小孩很少进去,一年级的时候,代表学校在公社大会堂表演过《打靶归来》集体歌舞,另一次就是小学老师带着我们全班去公社讨说法,至于他为了什么,我记不清,反正不是为我们或学校的事。
图:原安仁邮电所用房,门前邮筒仍在(摄于年)
每到粮库收粮、收蚕茧、收猪等季节或者是赶“高家会”的时节,百多米的长街都是四乡八里的忙人,还有许多操着外乡口音的驾驶员,大家都会到街上的安仁饮食店(综合商店)吃饭,有闲的来一份片儿川、光面,没时间或囊中羞涩的直接称几个馒头充饥。母亲就在这家综合商店做会计,但一到忙季,也放下手中的算盘、帐本,和店员一齐去搓馒头、称馒头,我就是坐在小山样的馒头堆里被拉扯大的。店员有些是来自城里的姑娘小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店里不仅做馒头、做豆腐、酒菜面饭馄吞小吃一一俱备(所以也称安仁饮食店),店里还有糖烟酒、虾皮鸡蛋等付食品,买的多数东西都要凭票,我小阿姨当时就在付食品柜台。大约在年左右,店里甚至在后院开了一家棒冰厂,一帮年轻人买了一台很大的棒冰机,捣鼓一阵子后生产一些简单的白糖、赤豆小冰棍,记得试运行时,我品尝过一根极苦的冰棍,据说是盐水冷冻剂不小心漏进去了。一些年轻人骑着带木箱的自行车来批发了去买,靠木箱里的棉花材料给冰棍保温,通常卖三四分一根。
综合商店的旁边就是供销社,这里面卖的东西要大件些,柜台干净整洁,记得有布匹和连环画卖。
图:原安仁综合商店(摄于年)
四
最热闹的地方自然是火车站,否则怎么叫“站里”呢。除过路货运列车外,一天有四班固定的客运列车停靠,龙游方向来经安仁到衢州还要经过南山、樟潭两个站,八十年代火车速度也远无法与现在比,被汽车超过是常有的事。火车到点,聚焦在小小候车室里的人相当不少的,买票得把脑袋伸在一个小拱门状的窗口才能望得见售票员。粉红色的小卡片车票要被检票员卡出一个M型的小缺口,才能进入站台上车。出口在站台的右侧,有人验票,在这个地方,有个场景一直印在我幼小的脑海里至今:几个铁路民警将一老妇女的鸡蛋和篮子夺了丢在地方,一起把人按在地上,说是投机倒把,一地的碎蛋。当时的年纪,我们小孩都不太明白投机倒把是什么意思,只知道是平时用来骂人的坏话。
车站是个不小的机构,有站场、候车室、卫生所、家属房,曾经还有过铁路小学,车站的值班管理室里是神秘的地方,一人高的控制面板上画着有许多规整的线路,红灯、绿灯闪亮着,铁路管理人员严肃地在这里迎接着着南来北往的列车,所有的铁路工作房里都会有煤炉,烧着最优质的散煤,在冬天里让你从头暖至脚,煤炉的上面不分昼夜总是烧着一壶水,当时就觉得铁路是大土豪。整个站场东西都安装了大喇叭,用铁路特有的语言报着来往车次并指挥工作:拐拐洞马上进站...
图:原安仁站铁路候车室(摄于年)
我是铁路子女,但不属于火车站,铁路系统有许多分支机构,管站台客运、货运的通常称为车务段,工务段负责铁路线路及桥隧设备的保养与维修工作,另外还有什么信号段、电务段提供电力和信号(相当于现在信息化)支撑等。安仁当时不仅有列车客运、货运,还有一个养路工区(工务段的基层机构)和一个信号工区。信号工区的家属房最后建,在站务和养路工区的家属房中间,衢州的铁路业务多归金华管,所以每一幢铁路相关的建筑中都有“金建台”三字,后面还有编号,,这是铁路建筑段给每幢房子的编号。
五
铁路家属房是供铁路职工及家属生活居住,安仁当时大约有五六座,都是一层的,每座通常六七户人家,统一的墙砖,非常牢固,每户通常是一室一厅一过道。在这标着“金建台”的家属房里我度过了童年,直到去城里读四年级,我的父母更是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和记忆都留在了这里。
图:铁路家属房(已废弃,摄于年)
我们的左邻是一对夫妇和男孩,男的是那个时代极稀罕的大学生,斯文得听不到什么声音,女的是龙游人,男孩叫德德,虽然比我大,但因生病时开刀在身上留下了像武装带一样的疤痕,显得瘦弱和木讷,我也属于瘦弱的,难得碰到个更弱的,没少参与去抓弄他,想想真是罪孽呀。右邻是神神叨叨的王师母,家里两个女儿都已经出落成大姑娘了,夫妻俩还经常吵架,老王是抗美援朝过的兵,平时声响不多,弄急了比谁都火爆,说的话不知什么地方口音,快得像外语一样。王师母精明且很能说话,一套套的,配合着笑着眯眼的表情很能哄人信服,有一次来了个扶乩占卜的,在晒东西的大朴蓝上拿棍支了竹箕,当时最兴的就是她,感觉她就是被附身的神婆,给我也占了字,反正说的就是好话。王师母是天生的信徒,最后皈依了基督。
图:铁路家属房(已废弃)
这排家属的尽头是赵姓一家,和我们家一样,也是两个男孩的四口之家,但他们家三个大小男人个个膀大腰圆脸大不说,眼睛和嗓门一样很大,至今看到眼若铜铃这个词,我也只能浮现出他们一家子的形象,家里的主妇虽然块头不及男人,气势上倒一点不输,发起威来眼也瞪得老大,但他家男人实在牛,吵起架来声若洪钟。
六
七八十年代物资仍然比较匮乏,铁路工人算是小镇上过得较滋润的,铁路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穿的制服除了颜色是蓝的,从大盖帽到衣裤款式都与部队或公安没有太大的差别,四季各式装备齐全,流传最广的就是印有“上铁”的大草帽,上铁即是上海铁路局的简称,这种草帽至今都有怀旧的厂家仿制。铁路工人们除了能凭“免票”证明乘火车、买到凭票供应的物资外,最让人羡慕的就是“供应车”,每月固定时间,会有满载生活物资的列车向沿线铁路工人按户分发物资,每家每户大小人众,提前拿着准备好的各种容器,来分发收到的物资,铁路里分派的物资质量一般都较地方好,连酱油都是浓黑郁香,小孩们通常负责干一些向自已家的油壶里倒酱油之类的事,烟枪们可以从分到蓝西湖、大前门。
图:年由樟潭供销社安仁分社发的购货证
尽管如此,为了更好地解决吃饭问题,多数人还都在家属房前后种菜、搭厨房的。我们家也一样在铁轨和家属房之间开辟了小菜园,菜园和家属房之间是道路,道路的上空也被充分利用搭了瓜棚,多是丝瓜和南瓜,南瓜的记忆让我刻骨铭心,长得实在太多了,尽管晒干的晒干、做菜的做菜,巨大的南瓜还是堆满了家里各种可能的空间,而这恰是我最不喜欢吃的菜。
图:安仁铁路信号工区宿舍(摄于年)
夏天晚上的瓜棚下是家属房的乐园,男人们闭着眼躺在椅子上吹着牛,女人们在门口就着灯光边做家务边聊天,孩子们在菜园边上奔跑嬉戏,不时有妇女对孩子的吼叫声。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台,当时是还不多见,可以聚焦几十号大人小孩,天没黑就预先有人来排满凳椅,看的是《加里森敢死队》、《霍元甲》,看到兴处,一列火车呼啸而过,一声悠长的压倒一切的汽笛声,在说话的、在骂孩子的,都只好无奈地停下,一定会有人把耳朵贴到电视上去听关键的对话,有时还会影响电视信息,主人冲上前拼命调整电视天气的方向,甚至用手拍不争气的电视,要是货运列车,四十五节,卡擦卡擦,开过去那可是需要点时间的。
当时的火车是烧煤的蒸汽机火车,家属房离铁轨不足十米,半夜里有火车经过,房子和门窗就会早早发出抖动的声音,有节律的声响渐大,直到远去,住在这里的人们都早已经练就在巨大声响中安然入睡的本领。货运火车的车厢有一些是开放式的,可以看到的是一车车的煤、木材和化工原材料。当然,对孩子们,最兴奋的是看到运武器列车,中越战争其间,开始是一列列拉着坦克、榴弹炮的车向西而去,后来是一列列的运兵车自西而返。
铁路工人们是辛苦的,尤其是养路工人,大清早就得趁着还没太阳出工,在他们的基地-称为工区集中后,像部队一样进行集合训话,明确任务,除了作为指挥员的“工长”等少数人可能留下值守,大家就扛上各种工具沿着铁路去工作,工作大体是线路维护,夏天尤其辛苦,只看父亲他们回家后脱下的工作服就可知一二了,衣服干了湿、湿了干,上面会带着汗水结成的盐花。我也是偶尔去他们工作的现场送饭才知道,平时衣着光鲜威风的父亲干起活来是这么狼狈艰辛。
七
父亲下了班是很注意形象的,头要梳到整齐发亮,后来条件好了还上头油,皮鞋是一定要擦好几遍直到发亮,不是一般的那种亮。衣着也干净整洁,穿皮凉鞋还要穿丝绸袜,据说曾因为这个被领导讽谕过,在这点上我没有得到一点遗传,父亲好不容易把我全身上下整饬得干净洋气,一转身我就能脏兮兮。
图:杂草丛生的原安仁铁路工区(摄于年)
当时父亲让我记忆深刻的事情是他居然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屋后我们自搭的厨房里开始写书,写的是铁路线路专业方面的书,用清晰的隶书在16开大小的纸上横写着,并用复写纸复成几份,写完一本会用帐本一样的硬面装订成一本,印象中写了好多本,基保有不少示意图,父亲烟瘾较大,写书时陪伴他的除了满屋的蚊子就只有烟,写字、抽烟思考、打蚊子,不断重复。买烟不光花钱还得要烟票,他当时好象二级工,钱还不如母亲的三级工多,就自己弄了个小木盒做卷烟,买了烟纸,烟丝,铺好纸和烟丝,一抽就成了一根烟,粘上就能抽,我也试着做过。
父亲爱赶时髦,喜欢听戏曲相声和流行乐,有一天可能是刚发了工资,兴之所至就坐火车到城里背了一套红灯收音机和电唱机回来,音质相当好,隔壁邻居都听得很清楚,周末,小家被母亲收拾得干干净净,蚊子飞虫也被挡在外面,家里的的水泥地面会用水得没有一点脏东西,是周围为数不多需要脱鞋进入的人家。马季和姜昆的逗人相声、苏晓明和蒋大为的美妙歌声便萦绕在这铁路旁简陋又温馨的小屋里,不过我通常是需要练字或做作业的,做完了也要早睡,那怕隔壁精彩电视剧的对白能清晰地传入我的耳朵,是不是很郁闷?
安仁铁路家属房(摄于年)
父亲平日话不多,难得碰到开心的朋友来,喝点小酒就会开心地聊起来,酒量不佳但爱喝得热闹,满面通红地划拳助兴,他有一根手指因在工作中被压机的铁件弹伤而永远不能完全伸直,划拳的时候显得很特别。城里木材厂的香亭姑父与他甚为投缘。周末,香亭姑父从城里坐上火车来家里,聊薛仁贵和岳飞、聊铁路里的传奇故事,俩人可以喝到下午好几点。
父亲做过宣传员,参加过铁路文工团,写几个毛笔字是很可以看看的,有次大概快过年缺钱花,动脑子写了许多对联,洒上金粉拿去卖了不少钱,于是我们一家的新衣服都有了。
八
母亲小学毕业考上全市最好的学校衢州二中,但初中没读多久就因为舅舅得了脑膜炎缺钱治病不得不缀学回家,之后就一直在供销社系统工作,算盘打的那叫一个啪啪响,是店里是业务骨干,做事麻利果断,能拿主意,是老经理重点培养的对象,店里大小事情都有份,盘点货物到半夜也是常有的事,有时我就在店里的长凳上吊着睡着,好在我小阿姨也在店里,跟着她蹭吃蹭喝的日子也着实不少。
家务活差不多也是母亲包掉,洗衣服和搞卫生任务最重,家属房的尽头有一口井,傍晚时是妇女们(铁路上称他们为家属嬷嬷)洗衣服聊家长里短的好地方,我有时会被“征用”负责专从井里拎水供母亲洗衣服,我力气不够大,绳子拉一段要踩在脚下再去拉下一段绳子。母亲的勤快一直是公认的,每天都要在井边花很长的时间洗洗洗,用板刷狠命刷,用棒槌使劲槌,像与衣服有仇似的,铁路工人的衣服实在是太脏了。由于没有浴室,夏天多数男人(包括一些小男人)会在井边洗澡,拎了一桶又一桶的水往身上冲,凉凉的井水,是需要一些勇气的。
弟弟出生时我已经上学了,忙碌的家庭连我也得承担一些简单的活,从哄娃、看着炉子上的开水、粥饭,慢慢的开始灌开水、提井水、烧饭、擦地、去工区拿蒸好的饭、到车站旁的小牛家买油条然后用一根筷子串了回家。夏天放假在家帮弟弟洗澡,然后带着他穿过一排排家属房到店里,可以得到母亲满意的表扬,然后人手一根冰棍,吃起来特别甜。
图:原安仁饮食店正对面的废弃房屋(摄于年)
尽管这样,弟弟最终还是得经常寄养在店对面的金珠娘家里,金珠娘是个较为典型的农村大娘,精气神都好得外溢,她嗫嘴发出一串声音,很快能把她家养的鸡聚在一起吃鸡食盘里的饲料。弟弟也过了一段较为粗放的幼儿期,常和金珠娘的鸡鸭扯混在一起,然后就是跟着她去铁轨边上去捡列车散落的煤渣,或是在街上捡棒冰纸-油油的有层蜡,是很好的燃料。弟弟的脸也长得粗放起来,红通通龟裂成一块块,哭起来也一样的响亮霸气。
家里是离不开操心的母亲,有一次她去城里培训,父亲给弟弟洗脚加水时先加了开水,不管不顾的弟弟直接将脚伸了进去......
九
上小学的第一天是有仪式感的,白球鞋、表示考分的油箱加鸡蛋,背着农村孩子少见的书包,到学校才发现,农村没鞋子穿的娃都有不少,我的土豪样显得与人民群众格格不入,这是一个人们还常把“贫下中农”自豪地挂在嘴边炫耀的年代,我因为穿戴过于整齐和正式常被同学取笑也属正常。
学校先是设在郑家村南头的一户农民家里,大木黑板被支在堂前,学生是没有几个的,教过我的有和蔼漂亮的方老师,还有一位是村干部初中毕业待业在家的女儿。很快村里在村最北面带出新盖的三间平房做为小学,还在门口平整了块百来平米的地当作操场,可以玩老鹰抓小鸡。班级也有了两个,都是复式班,我居然戴上了三条杠,六一节的时候,带着队伍唱着《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和《乡间小路》,走到几里外的中心小学参加活动,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一次三条杠牌子丢了,父亲怕我失落,硬是在家里给我做了一个出来,说起动手能力,我真的是家里最差的一个。
图:原欧塘小学(摄于年)
后来母亲不知道想了什么办法,把我转到在欧塘的中心小学,路是更远了,学校很大,每个年级都有甲乙丙三个班,每天早上天还漆黑,母亲就得起来为我准备早饭以及带去学校中饭的菜,然后我和隔壁赵家的大眼睛公子等两三人一起徒步(那个年代,有不徒步的吗)沿着两边都是树的堤坝乡道走到学校,每天都得拎着饭盒和用来带菜的搪瓷杯,学校只管提供蒸饭的服务而已,由于没有专门吃饭的地方,我们便将蒸好的饭和家里带的菜拿到村边衢江旁大樟树底下吃,大樟树已经不知道存在了几百年了,根盘得河边岸上到处都是,五六个人都抱不过来,饭后没上课的一段时间是自由而快乐的,在这里吃饭是一种享受,每天最期待的就是午饭时刻。
图:欧塘的樟树(摄于年)
十
所有的小孩都是馋鬼,童年的记忆一定是与许多美食联系在一起的,我尤其是。安仁是蚕产地,桑椹紫的诱人,以至于让放学的我直接迷失在桑林里,直接母亲发动同事一起在放学的路上寻觅到天黑。蚕桶在油里炸了也是一等的美食,和小朋友们抓了知了放火烤,随着知了的惨叫声越来越小,特别的肉香味也越来越浓。粮站塘边不知道谁家种的豆子,也被我们一群熊孩子直接用火烧了抢着吃,留下一嘴黑的“罪证”。来自安仁农场的瓜子瓜,肉瓤有白或黄两种,汁多清甜,瓜子大而黑,直接开小孔挖瓤吃,剩下的薄空壳就做成西瓜灯、瓜子就在家属房的窗台上。就连家属房后面的鸡冠花,也经常被我折了花吸甜甜的汁。父亲在屋后种了一盘茉莉花,花开的季节每天我都能摘下芳香沁人的花朵给父亲泡茶喝。母亲和我有时会在漆黑的夜里在田间拿着电筒抓笨笨的癞哈蟆,别看这玩艺肉粗,可算是天然美味,比起当时昂贵且凭票供应的肉,真是性价比极高。
然而记忆最深的美味,那一定是从十几里地远的外婆家捎来的茴香油炸麻雀和茴香油炸虾,外婆是用茴香的高手,麻雀或河虾挂上面粉拌了碎茴香、桂皮,在油里炸得金黄,过了酱油,香、嫩、脆,这是记忆一生的美食,连着外婆。
四十年时光悠悠,往事已成模糊片段,串起来却都是岁月的珍珠,生怕在记忆中散失了,所以才有了这些文字。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